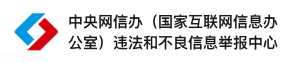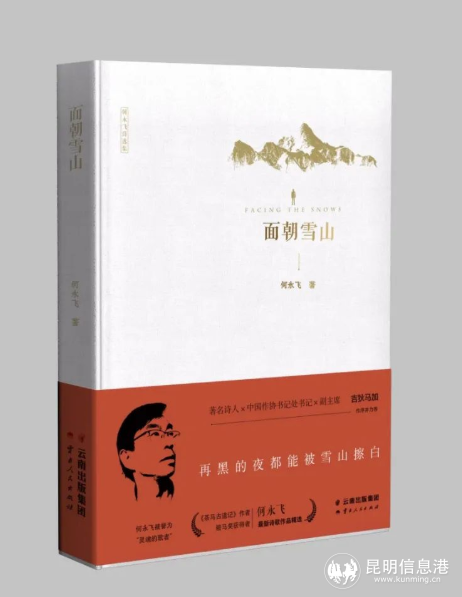
昆明信息港讯 记者陈秋月 近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吉狄马加作序并力荐的《面朝雪山》面世,该书是诗人何永飞的首部诗集,分为“我的爱”“春意闹”“洗骨记”“无字碑”“妙香国”“忧思录”六卷,所选诗歌都是备受读者喜爱和广为传颂之作。
《面朝雪山》以想象为翅膀,以沉思为力量,以大爱为轴线,抵达人性和人心的最深处,是面向雪山的赞歌。这些赞歌既有血有肉有硬骨,又有情有意有热度。诗人何永飞胸怀苍生和心生悲悯,他的诗歌在岁月荒凉处开垦和播种生命绿意,在沉浮世间寻找和拓宽灵魂路径。“再黑的夜都能被雪山擦白”,这是《面朝雪山》的诗魂所在,也是整本诗集的闪光精神所在。
何永飞,白族,生于1982年3月,云南大理人,笔名菩禅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次全国青创会代表,鲁迅文学院新时代诗歌高研班学员,被誉为“灵魂的歌者”。出版著作《茶马古道记》《面朝雪山》《穿过一小块人间》《神性滇西》《风过指尖》等十多部。诗集《穿过一小块人间》入选中国作协2020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多部作品获得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曾获第八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文学奖)、第二十五届全国鲁藜诗歌大奖、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长诗《茶马古道记》英文版(美国汉学家Saul Thompson翻译)分别由英国欧若拉出版社和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审美之“叶”与伦理之“根”:有关何永飞的诗(吉狄马加)
《面朝雪山》是何永飞最新的诗歌选集。一个“选”字,背后是诗人自我认同与外界阅读反馈之间双向的判断、梳理、总结、确证,既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示出诗人创作的谱系、理路、框架,同时凸显出我们对特定诗歌写作者最集中的印象与预期。何永飞留给我的诗歌印象,一直是鲜明且独特的。要建立这种独特并不容易。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通讯发达、经验膨胀、情感共享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与人之间、一种生活与另一种生活之间,可以用最小的成本、最低的能耗,产生最强烈的能量交换、形成最宽阔的内容交集。世俗生活之树因此而枝繁叶盛,但我们内在的精神景观,却常常会变得彼此近似、相互覆写,以致在某种意义上失掉了辨识度,或者说,难以找到自我表达的独特语词。这未必算得上什么不幸,但这的确是现代人的孤独。诗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对抗这种孤独,是为了树立起个体观看世界及生活的独一无二的角度,是为了找回自己的语词、乃至找回自己的语气。我想,何永飞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他的诗歌拥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征,他在诗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那片神圣疆域。他的诗歌写作是有根的,因而,也是有底气的。
在相当的程度上,这种底气,源自何永飞诗歌创作的“原生土壤”,也就是云南边地的独特自然环境、以及由此生发而来的独特人文景观。雪山、村落、江河、高原湖泊、荒野生灵,在何永飞的诗歌世界里是反复获得书写、绽放出独特光彩的对象。在他的笔下,洱海是宁静而有力的,能够使“硬的肠子变软,软的骨骼变硬”(《海舌》);雪山景观是标志性的,“悬崖上刻录着天地密咒……海拔3000米以上/每一阵风吹过,都会留下深深的痕迹”“雪山高过千年,高过尘俗/就像神灯,白光擦亮硬骨”(《扛着群山奔跑》);高原上的一条河,它的源头是“英雄的一滴血”“美人的一滴泪”“我的前生,或来世”(《河的源头》);天空飞过的苍鹰,则是“神灵的化身,衔着高原/穿梭于传说与现实之间/左边的翅膀是白天,右边的翅膀是夜晚”(《苍鹰》)。何永飞对这一切是熟悉的,正如他笔下写到的人们一样,擅于“在这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山水间行走”,甚至“能给天气把脉/还能辨识哪座山有善骨,哪座山有恶相”(《消瘦的牧歌》)。
这是何永飞笔下绚烂的、充满神话感的边地风景。值得注意的是,风景并非仅仅是客观的、物质性的存在。对风景的观看,是一种选择性、策略性的行为动作,一个诗人去写一系列“物”、写一种特定的风景,他的“写什么”与“怎么写”,背后定然是充满能动性的:那是从本性、从文化无意识中不断进化而来的主观审美选择,在文本中具化为独特的感受姿态及表达姿态。何永飞对自然生灵、对边地风物的书写,并不仅仅是向外摹画的、更是向内开掘的:许多人在评价何永飞诗歌写作的时候,都会提到“灵魂”这个词,我想,这指的正是此种“向内”的维度,指向由自然物象中不断投射或阐释出的,人内心的价值、坚守、力量和光芒。在诗人的理想世界中,“有不穿伪装的花草,有流水做的琴弦”“善念自会长出菩提树/……以清风,擦去尘埃;以绿色,修补尘世”(《菩提树的孩子》)。面对自然之神,一个人要交出内心的高傲与怨恨,以此“赎回春光、睡眠、慈悲泪/扶起踩倒的小草,原谅绊倒自己的石头”(《面朝雪山》)。他甚至愿意把自己的肉身交出,“将全身骨头,一根一根拆下/整齐地排列在草地上,用溪水清洗”,为的是洗去尘灰、惊恐和软弱,把洁白和坚韧“彻底还给骨头”(《洗骨记》)。
作为一位在自然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诗人,何永飞显然是在对自然的抒情和表现中,注入了其对人生与世界的根本的认知方式、表达途径、情感态度、价值判断。对诗歌而言,这一切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既是审美之“叶”、也是伦理之“根”。作为一位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何永飞的诗句背后,无疑是古老而巨大的、深具民族特性的审美习惯和文化伦理。例如,我们能从中看到超时间性的、来自古典时代的那种对生死的体认方式:“原来他高过白云,渐渐地又矮于泥土/他把死当作一粒种子,埋入自己挖好的沟里/第二年,野草葳蕤,长在他的上面/还向四周蔓延”(《山地里的孤墓》);“碑上的青苔/是生命再次前行踏出的脚印,去向自有安排”(《无字碑》)。《神临记》等长诗,则具有浓厚的民族神话色彩,人在特定文化视角下对世界及存在的理解,在其中得到了集中的彰显。不同于现代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分类学思维,何永飞在诗里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世界、祖先世界的同一,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万物之间并无分别之心,不仅可以对话、甚至能够混淆:“他人的命,也是自己的命/没有青草的舍身,很多动物的牙齿/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会消沉,会灭绝”(《大地悲心》);“怀着仇恨的人睡去,星辰与草木对饮/……陷入尘俗的人,与端坐时光之外的雕塑/互换位置”(《在洱海边》)。这所谓的混淆,是一种“隐身”的技巧、是找回自我的方式:“火隐于水,风隐于天空/……我以变形的方式活着,去迎接神圣的死亡/我死后,就隐于聋哑之石”(《隐身术》)。这是“术”、也是“道”,它擦拭出极具民族性、地方性的表达逻辑和审美特征,也不断划定、拓展着诗的领地。
当然,何永飞的诗里,除了“古老”、也同样有“当下”。他能够把高原景观同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结合在一起,“筑路人的硬骨,擂响高原铜鼓/……金色的种子,将贫困一层层撕去/将山间的白昼一层层拓宽”(《云上之路》)。《普拉河》《滇西安魂曲》等诗作,则处理了与当下生活一脉相连的地方历史(如茶马古道往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滇西大反攻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何永飞诗歌更加丰富的层次感和多元性:他的写作,可以是“虚”的、也可以是“实”的,可以是浪漫属灵的、也可以是现实落地的。这正是优秀诗人所应具有的品质。(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净魂,或唤醒(后记)
面对一群豺狼虎豹,而心所无畏惧;面对一只蚂蚁或蝴蝶,而心生敬畏。这应该是写诗的最佳状态。
与诗相伴,或说在薄薄的人生册页上耕种诗意,已有二十余年。从懵懂年少,到而立之年,再到不惑之年,一路走来,有辛酸,也有甜蜜;有悲伤,也有欢喜;有失去,也有收获。诗歌一度成为我生命的出口,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我都学会了坚强或坦然面对,相信上天在给一个人承受苦难或恩赐甘露,都有其用意。走出茫茫黑夜,就会与黎明的曙光满怀相撞,同样,当享尽一天的明亮,我们又不得不再次被黑夜包围。人类在不断往前,可世间的很多东西不曾改变,特别是本质方面,其总是在往返循环,或隐,或现;或急,或缓;或原貌出场,或有所改装。明白这一点,对自己起起落落的命运,就会少了一些抵触情绪,多了一些向上和向善的力量。
写诗者,首先要修好自己的心。心,诗歌之源。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心有多美,世界就有多美。如果心不及针眼,如果心黯淡无光,那写出来的诗句也就有狭隘性和危害性,难以打动读者,难以流芳,难以达到诗之功效。当然,也有一种人,能以虚情假意,写出看似美妙之诗,还得到了一些不知情读者的吹捧,可一旦被揭穿,或经过时间的淘洗,其魅力和生命力就会消失殆尽。自作聪明,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起初写诗,我并没有思考太多,只想通过诗歌的方式将内心积压的忧虑和苦恼释放出去,既而获得轻松感和愉悦感。应该说,我写诗一直是用心的,都发乎于心,只是格局和境界不高,过多地囿于“小我”,缺乏“大我”精神。所以,我必须转变,必须突破自己,必须找到一条更加宽阔的诗歌之路。
做到“大我”,最重要的莫过于打开心量。这也是我在修心和修行过程中所努力的。谁都有自己的窄小和薄弱之处,因碍于情面,或有别的担忧,不敢公之于众还能理解,但面对自己就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正视并完善才是明智之举。与人为善,历来是我做人的根本原则,可我承认,之前自己的胸怀还不够宽广,对某些不公平之事总是耿耿于怀,对某些不守道之人总是感到愤恨,甚至有时还会产生偏激的思想。后来,经历得多了,终于有所觉悟,凡是需要去包容,正所谓有容乃大。忍辱,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考验,也是衡量能否管控得好自己言行的关键所在。活着,为自己并没有错,可也不能只为了自己。众生皆平等,万物皆有灵。这样想,我们就会逐渐放下内心的傲慢和偏见,就会与他人、与一切和睦相处。现在,我不再活得那么纠结和痛苦,因为我不再轻易动怒,不再妄加定性,更多的是往后退一步,进行反思和反省。就算是伤害我的人,都回赠给他笑容。宽恕别人,等于宽恕自己。心系苍生,观照灵魂,我才不愧对被大家称为“灵魂的歌者”的美誉。
诗歌是圣神的,这毋容置疑。而写诗何为?的确需要我们深思。如果把写诗仅仅当作娱乐和消遣,那就是对诗歌的一种轻蔑,或亵渎。写诗者,应该摆正姿态,不可高高在上地俯视,也无需显得过于卑微地仰视,最好选择平视。跟风赶潮和人云亦云是写诗之大忌,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不良风气带坏,会被肤浅的表象迷惑,从而写出来的作品没有自己的风骨,也没有厚重感。我之所以行走在喧哗的边缘,之所以或敬畏或无畏去呈现和揭开天地间的一些截面或碎片,就是不想迷失自我,不想以美好的形象活在残缺的地方,或以残缺的形象活在美好的地方。我写诗,不会空洞地赞美和歌颂,不会对有些苦难和隐患视而不见。当然,我没有任何图谋不轨之意,不会无情地撕碎艳阳和春风,不会无端地摸黑时代和历史。我只想让明丽或灰暗、温热或冰凉、激昂或低沉、抽芽或滴血的诗句,洗净落在我们灵魂上的尘埃和杂音,唤醒我们内心的善念和悲悯。
我虽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可也自知才情有限,再加现实的残酷,没有十足的信心和底气。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诗歌的热爱和追求,也不影响我对尘世的迷恋和担忧,生命不息,我就不会停下奋进的脚步。正如我在一首诗中写道:“也许,哪天这无用之诗/还真能救起一个落水灵魂”,真希望有这样的时候,但更希望没有一个人的灵魂不幸落水。
《面朝雪山》收录的诗歌作品,都是从“骏马奖”获奖作品《茶马古道记》之后我所写的数百首诗歌中精选出来,有些还作了很大的修改。诗路上,我总是遇到贵人,比如给予我温暖关爱的晓雪老师、吉狄马加老师等德高望重的前辈,比如读懂、读透、喜欢我诗歌作品的评论家和读者,比如默默支持、鼓励、关注我的亲人和师友。要铭记和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我定会好好珍惜每一段缘,珍藏每一份情和爱,并以此为动力,在诗歌的天空,永远飞翔。
何永飞
2021年11月写于禅石阁

《面朝雪山》定价82.00元/本,免快递费,喜欢的朋友可以加作者微信hyf9920购买,请注明“购书”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