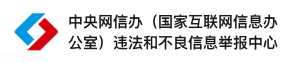品读
悲观的理想主义者
周明全印象
文 | 王晶晶
我和周明全是三年前江苏作协和盐城师院合办“文学双月谈”时认识的。那次双月谈请的批评家有周明全、宋嵩、程旸、黄玲,青年作家是陶林和严正冬,我作为大学一方的协调者,叨陪末座。
那段时间是我回国后最忙碌的一段时间,那几天忙着另一个会的会务、上课、期中考核、深夜修改论文格式投稿,恨不能立地睡着。那天上午另一个会议的代表刚离会,下午明全他们就来了。晚饭陶林早早赶去作陪,我这个累瘫在家准备发言稿的出门障碍症患者则一拖再拖,眼看就要拖到晚饭结束了。幸好陶林坚持,不停问到哪里了。
等我赶到,桌上寥寥几个菜已经吃得差不多。我道声失陪,就说再点几个菜。只见明全犹豫了一下,问,可以再要点酒吗?我说可以啊,点了两小瓶啤酒。明全默默不语。
添酒回灯重开宴,喝了两口啤酒,大家活跃起来。我事先看到名单,以为《大家》的主编是位德高望重、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文艺中年,完全没想到是眼前这位身穿牛仔衣,有几分落拓不羁、谈笑风生活灵活现的80后。确认过同为80后,大家仿佛一下子亲近起来,渐渐无话不谈。酒阑茶尽,意犹不足,不知谁提议夜游。我瞥了一眼包里没看完要发言的小说,迟疑半晌,被稍一撺掇就高高兴兴同去了。
明全显然看上去比我们都成熟,可以说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和他的工作经历有关。而他为当代批评做的贡献,编选70后、80后批评家丛书、做系列对话……我是直到身处会议现场,听了主持人介绍才知道的。
那时他正在写《中国小说的文与脉》里的文章,后来这本书获了2020年南方文学盛典的“年度文学评论家”奖。授奖词里称他的文学批评“感情充沛,潇洒不羁,放胆为文,直白其心”,实在是他为人为文的真实写照。
因为对中国小说共同的兴趣,我一向关注他的研究和评论,第一时间读了他的新书。书中对中国小说伟大的传统有许多创造性的发现和讨论,扎实而有趣,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例子,给我很多启发;而对当代小说的评论又大胆锐利,妙语连珠。尤其可贵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始终保持着真实的锋芒。在我看来这是殊为不易的,学院的体制造就了符合一系列理论和程式的批评,唯独缺少写出真实感受与判断的要求。长此以往,我们或许已经不习惯把握并表达真实之思,哪怕我们希望这样做。但是在周明全的批评中,我始终能看到他的“自心”。
他的诚实一面使他不绕过中国小说理论建设的难题,又使他在评论作家作品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在这个时代,我们似乎更多习惯强不知以为知,尤其难做到于无疑处有疑,作为批评家,周明全却敢于说出他最真实的阅读体验。至于他文字的机智聪敏、妙趣横生,一如其人。应该说他的文章和他诚实有趣的人格一样可爱,一样天才,而后者比前者更可贵,更富有魅力。
我一向知道他是个每天接送宝贝女儿上下学、周末送辅导班、每天给家人买菜做饭的女儿奴,是个留着长发、喜欢抽烟喝酒、逛旧书摊的兴趣单一的男人;而我一向好奇,这个对中国小说执着求证的研究者和妙语连珠的评论家是如何穿梭于他的日常生活的。
直到今年清明节,我才有机会趁着到昆明开会,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
他的办公室,一书架、一桌、一椅、一沙发、一茶几。书架占了整面墙,塞满了书。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几块旺旺雪饼,旁边的字纸篓里还有不少雪饼的包装纸,和排山倒海的精神食粮相比,他的物质食粮简直草率简单随便到可怜。
开完会后一天,他带我去郊县他朋友的农场,算是尽了地主之谊。他同时招呼前去的还有退休的高官、从政的美女、失意的大学教授、经商的小说家……都是他的朋友,周明全似乎天生具有让朋友们互相认识的热情和让大家皆大欢喜的能力。这是我第一次到云南乡下,到时正吃午饭,流水席上满桌新鲜的牛羊肉、米汤、甜酒,还有山野里的菌子,简直比我们的年夜饭还丰盛。主人正介绍某种菌子的珍贵,明全就起身拨出半碗菌子帮你拌饭,嘴上却说可以了,要不然等一下你会一直看到两个周明全。
农场漫山遍野鲜花果蔬,鸡鸭满山、肥牛成群,鱼儿跃出鱼塘,主人摘下果蔬、到鱼塘网鱼,让客人能拿走多少拿走多少。我想说,如果没有看到周明全坐船捞鱼的场景,便不能更真实地了解他——我必须把这段见闻贡献出来,否则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鱼已经由众人从鱼塘起到网里,只见他穿着不知从哪里随手拿来的破雨衣(上面印着某某农药的广告),坐上一艘破旧的水泥船,划船去渔网里捞鱼。仔细一看,他手舞足蹈、奋力划向前的船桨竟然是预备捞鱼的一根长柄的舀勺!我们在岸边差点笑岔了气。
追求真实、表里如一(俗称不装),这在很多人可能是所谓的人设,但对于周明全来说,他可能压根不懂什么叫人设,他就是他,我们看到的便是真实的他,也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也诚实率真、为朋友不遗余力。这可能是他最可爱的地方,也是他的文学批评最可爱的地方。有的人让人看到真实的样子便人设崩塌,而周明全属于那种你越看到真实的他,越觉得人性动人的人。追求真实使他不停反思,时常怀疑,他是理想主义者,却并不乐观。作为朋友,我由衷希望明全始终面带他坐在捞渔船上挥舞长勺时露出的、堂吉诃德式的开怀笑容,战胜永恒的虚无。
本文作者:
王晶晶,2013—2016年任丹麦奥胡斯大学社会与文化系讲师、研究助理,2017年至今任教于盐城师范学院。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客厅内外——林徽因的情感与道路》。

品读
自称“野狐禅”的周明全
文 | 雷杰龙
一日,和一位云南文坛上广受尊敬的兄长喝酒,他突然问,你和周明全关系怎样?我说,很好啊,经常一起喝酒。我奇怪,问他为何有此一问。他说以前不了解周明全,最近和他喝过几次酒,觉得他不错,可以当兄弟。
我明白那位兄长的担心。文人嘴碎,涉及作家、作品,大多直抒胸臆,口无遮拦,少不了文字江湖上的刀枪烦恼。周明全是云南近年崛起的青年批评家,是云南文坛的“新贵”,涉及具体的作家、作品时,他作风泼辣,不留情面,无端招惹的是非自然不少。在那位兄长眼中,或许,我也是一个傲慢无礼、尖酸刻薄之人,他担心我和周明全会掐起来。在他眼中,文人互掐,无端消耗是一件可悲之事,他希望云南年轻一代文人们能互相包容,最好能亲如兄弟,这才能让云南文学的生态环境更好一点点。应该说,那位兄长的担心并非毫无由头,但他对我和周明全的担心却是多余的,因为在他担心之时,我和明全早已是兄弟。
和许多人一样,我和明全的兄弟之情始于酒桌。明全好酒,我不好酒,但却善饮,一起喝酒,大多能够尽兴。但作为同行,如果没有“道”上的交流与契合,喝再多的酒,也不过是酒肉朋友,是不大可能成为兄弟的。
和明全,一次次喝酒,其实是谈读书。情感的增添,也大多是在谈读书中发生的。最终成为兄弟,酒只是助缘,真正的因缘,其实是文字。
和明全刚认识的时候,每次喝酒,他总是很兴奋,说他最近又读了某本书,于是就听他讲那本书。由他谈的那本书,我联想到自己读过的某本书,如果他没读过那本书,就会认真听我说那本书,并且掏个小本子出来,记下那本书。过些时日相遇,他会兴奋地说,读过我前次说的那本书了,接着就兴奋地说那本书。我有点吃惊他竟然真的去读我说的那本书,并且读得很靠谱。朋友们聊天谈读书,一般也只是过过嘴瘾,事后能像他那样去认真读书的真是少之又少。正是他那样的读书劲头,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知道他是一位真爱读书,真爱文学的朋友。况且,我还知道,那些年他在云南人民出版社从事行政工作,他上的是一所我认为并不靠谱的大学,他所学专业也非文学,而是绘画。但他身上没有一点行政气,也没一点画家味,要说有什么气味的话,除了酒味,就是书卷的气味。只是,那时觉得他的书卷味还不强——他还像一块新鲜的海绵,正在拼命吸收着书卷的气味。
2015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的书。这是一本明全专访和综述80后青年批评家的书。作为一名小说写作者,我也关心前沿批评家们的思想潮流,但在这本书出来之前,我关注的视野只到70后批评家。这本书给我提供了一个关注80后批评家的文本,我认为明全眼光独到,行动有力,为文学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正是这本书,帮助我开始重视80后批评家的思想成果,拓展眼光,除书中那些人物之外,通过他主编的《80后批评家文选》《80后批评家文丛》等书,关注了王晴飞、李振、方岩、黄德海、岳雯等一大批优秀的80后青年批评家。
数年前,周明全出任《大家》杂志主编。因为《大家》杂志的特殊性,这是一件引起文坛关注的事件。上世纪90年代,高举“先锋”大旗的《大家》杂志横空出世,创造了不少当时的文学“事件”。之后,《大家》历经波折,它的命运,就像先锋文学的命运。这么一份重要的文学杂志压在80后的周明全身上,作为兄弟,有点为他担忧。不过,此时的周明全,早已不是十余年前我认识的那个周明全。通过多年的刻苦阅读、写作和历练,他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批评家和文学工作者,我相信他定能胜任他的工作。
周明全到来之后的《大家》杂志,给我最大的感觉,便是回到文学的常态,不再强调所谓的“先锋”。或许,这么做,有收敛和保守的嫌疑,但能抛弃早已消亡的先锋,本分地回到文学的常态,又何尝不是一种睿智和勇气呢?正如著名翻译家柳鸣九先生观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的文学现象时所言,那时的法国和欧洲(其实也是世界文学),所谓的文学流派已经走向消亡。各种文学流派已经合流,经典写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既互相影响,又相安无事,各自独立。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和未能产生一个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学流派。这就是说,《大家》杂志诞生时高举的“先锋”旗帜,在当时的世界文学潮流中早已偃旗息鼓。如果说当时的“先锋”旗帜尚有意义,那不过是当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还有时间差,“先锋”的目的和意义,正是为了补上那个时间差。用一次和明全兄喝酒时他说的话便是,如今,那个时间差早已补上,《大家》杂志还要那么面破旗干什么,难道老老实实回到常态,回到文本就办不好《大家》杂志吗?对文学,我相信的永远是人,是作家,是作品,而不是标榜的某个流派。
我欣慰于明全兄的从容和自信。他在自己的《中国小说的文与脉》中写了篇后记,名叫《我是批评界的“野狐禅”》。如果仅以文学出身而论,他说自己是“野狐禅”并不为过。不过,这位“野狐禅”的批评家如今早已书卷气十足,谈读书时早已能和我说,杰龙,我觉得这本书你应该读一读,那本书你也应该读一读。一次喝酒时,他又和我说,杰龙,你发在《人民文学》那篇小说《斗鸡》来自唐传奇的《东城老父传》,我最近读到一个唐传奇《吴保安》,牛肃写的,我觉得你应该改写它。你是大理人,你把故事背景放到“天宝战争”里,一定能写成。和我这么说的时候,他从包里掏出一份《吴保安》的打印稿递给我。这是给我派任务啊!结果,根据那份两千余字的打印稿,我写成了一万八千余字的短篇小说《记骨》,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这位80后的批评家,已经能给我这个70后的小说写作者派任务,如果他以参文学为“禅”,那他的“禅”早已不能说野了!
本文作者:
雷杰龙,供职于《边疆文学》杂志社。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钟山》《花城》《江南》《大家》《诗刊》《滇池》《当代文坛》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百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