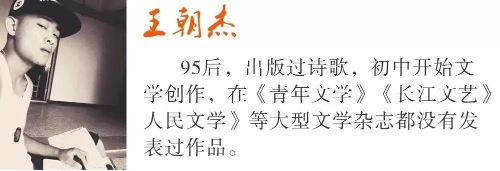有一天,一个叫三夫的骗子游历到了昆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他认识了一个叫夏桥的姑娘,夏桥是一个文艺青年,在昆明的大学里读书,读的是化学系,却崇拜一切和文学有关的事物。
三夫不是一个被通缉的骗子,也没有干过杀人放火的行当:在高级宾馆当点心师用的是最差劲的奶油,在国企当会计帐也做得一塌糊涂、用假证在幼儿园当老师上课翘着脚看王小波的《白银时代》。
后来由于全班学生的考试成绩都不及格,三夫从教师队伍里被踢了出来,走时还多让学生们交了120块的欢送费,他不去酒吧,不爱夜店,活的不像个年轻人也不像个老人,他把自己归类为骗子,演什么像什么,在这样一个年代,他基本上是个异类,走到哪儿混到哪儿。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代,三夫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某条沙尘滚滚的乡村土路上,在某个破烂拥挤污浊不堪的长途客车上,在一列逢站必停的最慢的火车上。
至于三夫的年纪,是21岁,高中连跳两级,大学只用了两年就学完了,谁知道家中遭遇变故,说他父母双亡有些夸张,他父母身体还好,因为他是领养的,据说他的亲生父母,一个吸毒一个抢劫,他后来才被领养,三夫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对人生颇为怀疑,第二天留下一张纸条就从家里消失了。
夏桥比三夫大两岁读大四,但三夫说,我25了。
夏桥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毕业考试和无所适从,可她还是参加了文学社的活动。那天,他们在学校多媒体室里参加文学会,讲得是现代诗歌,说是多媒体教室,其实就是多了个投影仪的教室。三夫一下子就把夏桥震住了。
三夫说,我不知道自己生在哪里,所以我要让这个世界听见我的声音。那时,夏桥没有看过《樊城似海》,不知道那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模仿。
然后,他热血沸腾地为他们朗诵了他最新发表的长诗——《虚无主义的树》中的一节:
也许,我是天地的弃儿
也许,盗贼是我的父亲
也许,我母亲分娩时流出的血是有毒的
它们流淌至今,也就变成了我生命里的愤怒。
至于三夫怎么会出现在夏桥的文学会上,这也是一个骗局,因为会上的人都不认识三夫,三夫一天前来学校送衣服,他最近一份职业实在一家做文化衫的公司送货,他骑着前灯被撞烂的电动车进了大学,送货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些文化衫上写的是“伊娇,我爱你。”一共21件,接货的男生说,自己要让好朋友都穿上这些衣服,晚上8点自己要给一个女生表白。
三夫冷笑了一声。
晚上8点,三夫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学校,在学校绕了一圈才找到21件文化衫,他把车停下树下,坐在车上点了一支烟,远远的看着这在21个人的起哄下,女生给了那男的一个拥抱,三夫之所以回来,是想看看是怎样傻的姑娘才会被这样一个没有水准的表白打动。
看到一半,保安走过来说,这里不准抽烟,你哪个学院的?三夫捏了烟,骑着车就出了学校。想着白天看到的文学社活动,拿出手机就撒谎病了要请假。
夏桥觉得,他太像一个诗人了。年轻的夏桥激动地想。他头发不长,脸色苍白,有一种晦暗的神经质的美,眉头总是悲天悯人地紧锁着。
他们有了一夜情,就在酒吧的沙发上。一群人,喝了太多的酒,酒使诗人情不自己。
她怀了献身的热忱,抖得像发疟疾。他很温柔。他温柔地、怜悯地把这洁白无瑕的羔羊紧紧抱在自己怀里,说道,“我的温暖,我的灵感啊……”
他告诉夏桥,自己是个搞文化创作的。
夏桥落泪了。
三夫常带她去看滇池。她就是从那时起爱上了滇池。他站在坝堰上,眺望滇池,说,水真他妈绿,不过有种大海的感觉。
夏桥附和道,我觉得也是。
防风林带在她视线可及的远处,绿得又端庄又单调。蓝天、白云、黄水,偶尔飞过的水鸟,她觉得人生人生小小的幸福,就藏匿在这地久天长的、永不会开口的天水之间。眼泪会忽然涌上她的眼睛,又疼又甜蜜。她以为这一切将是天长地久的。
半年后,三夫说,你等我,我回一趟南京,我把一切弄好,我就回来找你,我们过一种不同的生活。
夏桥说,好。
她送三夫上了飞机, 三夫最后一条短信是,我下飞机了,从此电话关机,失去了联系。
起初,人人都羡慕夏桥的好运气,能够找到到那样一个堂皇的政府小学去教书。夏桥自己也是高兴的。
漫长的八小时上班时间,备课,解答小学生们问题,上班的生活就像沿着轨迹运行的列车一样周而复始,那一种平凡的单调对过惯平凡的生活的她来说还行。
夏桥常常一个人躲进图书馆室里,看书,写一些诗行。周围的女老师下班了就去唱歌,到处浪。图书馆里,书架壁立,灯光柔和,散发着饼干的香味。
那一段时间,她觉得书里每一首都像是三夫写的写在纸上的。就在这时主任找他谈话了,主任语重心长地问她,“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我们学校,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大家庭。”
此刻,主任苦口婆心地想了解这个姑娘不合群的原因。她从主任办公室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抬眼望着细长的优雅的拱窗,忽然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响起来,是一个神秘的祈祷般的声音,一下一下,撞击着她,她整个身体像钟一样发出嗡嗡的震颤与共鸣,那声音说,“别等了…他不会回来了”顿时,她眼睛潮湿了,她觉得是命运在和她说话。
主任给他给介绍了个男朋友韩江,是个大学教授,据说是最年轻的大学教授,人品端正,才华横溢,无不良嗜好。
那是一个节日的前夕,学校院子里,在分葡萄和带鱼,热闹,喧哗,喜气洋洋。人人拎着带鱼和葡萄回到办公室,一边议论着各自手中带鱼的宽窄、葡萄的大小。忽然有人在下面喊,“夏老师,楼下有个帅哥找你。”
夏江一起看了八场电影以后,她做出了一个地动山摇的举动:她决定和夏江在一起。
在一个安静的晚上,她一个人在房间收拾自己的东西。日光灯管嗡嗡地轻响着,是静的声音,不知为何让她想起正午时分阳光照耀下的滇池,他抽着烟看着她。一瞬间,她想,也许,不是没有忘掉的可能,和凡俗的生活、琐碎的日子和解,也许,这里有一些秘密是他不知道的,卑微却依然珍贵的秘密……她用手抚摸就要消失的拱窗,最后的拱窗。月亮悬挂在窗外,是一轮雾蒙蒙风尘中的圆月。“再见了,朋友!”她轻轻说,是对拱窗,或者,也是对这里的一切。
和韩江在一起半年,平淡无奇。韩江约夏桥一起去澄江,就他们俩,夏桥穿着裙子,美丽动人,韩江说,你先来我这,我收拾完东西我们就去。
夏桥进了门,看着韩江收藏的石头,颇为好奇,这动动哪儿摸摸。
韩江从卫生间里拿着洗发露往包里放,蹲下来盯着夏桥那丰满的臀,两步冲到夏桥背后,拦腰把夏桥从抱了过来。夏桥吓得啊啊叫,已经被韩江放倒在沙发上。
他把抱枕扔到一边,开始脱夏桥的衣服。夏桥躺着,连衣裙只能撩到肚皮以上,他转而脱夏桥的丝袜。夏桥喊:“韩江,你干什么?韩江,你要干什么!韩江,要死了,你干什么呀你!”
而在某一刻,不管她是否愿意承认,她的确想到了三夫,如果是那个温文尔雅的文化人,此刻他会是什么样子呢?他太哪儿呢,或许他从来没有爱过我吧,但她只用了百分之一秒就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了出去。韩江又含含混混地出声了。她听见他断断续续地说:
“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
“可我不想给你!”
“你个骚婊子!”
“啪!”夏桥一巴掌打在夏江脸上,“你给我让开,否则我报警!”韩江停下来。
“我要回去!”
“现在?”
“我永远不会见你。”
此时夏桥明白了,所有男人都是这样一个货色,他所有爱你,喜欢你,都是为了脱掉你内裤压在你身上那一刻,她知道他什么邀她来一起去澄江了。他是真有耐心,这么久才暴露,男人真是可怕。
这么一想,她不反抗了,哭得撕心裂肺。
手机响了。半分钟过去,夏桥才听出是自己的手机铃声。她在地板上摸索半天,拿到手里,铃声断了之后又响起来。是学生家长。她吸吸鼻涕,对韩江示意,别出声。
“夏老师吗?我是小彤的家长”电话里的声音尖细。
“啊——是。”
“小彤出什么事了吗?”
“咳嗽。”
“很严重?”“咳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那怎么办?”
“明天可能不能来上课了。”电话里的声音变得更尖更细,“要给她请个假!”
夏桥擦了把眼泪。开始推韩江,让他停下,猛一下把韩江掀到了地板上。她站起来抓起裙子就下楼,往卧室跑。
夏桥回到了宿舍。哭了三个小时。哭完点了个外卖,发个个朋友圈,你在哪儿。下面一大串浪荡子弟评论,亲爱的我在这,她丢开手机,顿时觉得这个世界无助又充满了虚幻。
过了几天,没有韩江的电话,夏桥主动给韩江打了电话,韩江那边嘈杂不已。
夏桥觉得喜欢自己这个男人,虽然不是很正派,但也不至于那么讨厌,男人嘛,食色性也,于是问:“韩江,我们的事你怎么考虑的?”
“你说……我该怎么考虑?”韩江低沉下来。
“你要是能给我一句靠得住的话……”夏桥靠着玻璃前,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认真地说,“你敢给我一句靠谱的话,我就把自己给你。有一天我们结婚。”
“不需要了!”韩江说。
“只要咱们一心一意的,可以做一对与众不同的情侣,你在大学教大学生,我在小学教小学生,有一个家,我给你做饭,你带我看电影”夏江给他宽心,“我不是那种不是人间烟火的女人,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还需要时间。”
“你怎么就不明白!”韩江烦躁的说,“我不过……和你玩玩……”
“你说什么?”夏巧腾地红了脸,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你说的话?”
“玩一下,你却当真了。”韩江仍然重复一句,甚至以可笑的口吻说,“就像我玩我们学校的女大学生一样,怎么能谈到结婚呢!还给我做饭。”
夏桥的脑子里轰然一响,麻木了,她自己觉得已经站立不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嘴唇和牙齿紧紧咬在一起,舌头僵硬了。
她不记得自己是怎样挂了电话的。
三夫刚下飞机,手机钱包就被偷了。不愧是南京,等三夫回了家,父母已经搬家了,他补了银行卡,多方打听才找到自己的养父母,他要干什么他很清楚,他找到了养父母,拿到身份证,他也拿回了自己复旦大学的毕业证,因为想要好工作,没有毕业证不行,他不能再漂了,他也不想做个骗子,他弄丢了夏桥的电话号码。微信他妈也被盗了。
两个月后他就回到了昆明,他恨自己,自己怎么就没问夏桥的工作地址什么。
他找了工作,这次不骗人。
夏桥,颓废了几天,突然想去趟滇池边,周末她打了车,走到滇池边,她看见了三夫,三夫说我每天来这里我在这里等了一年三个月。
我知道你会来这儿。
我爱你。